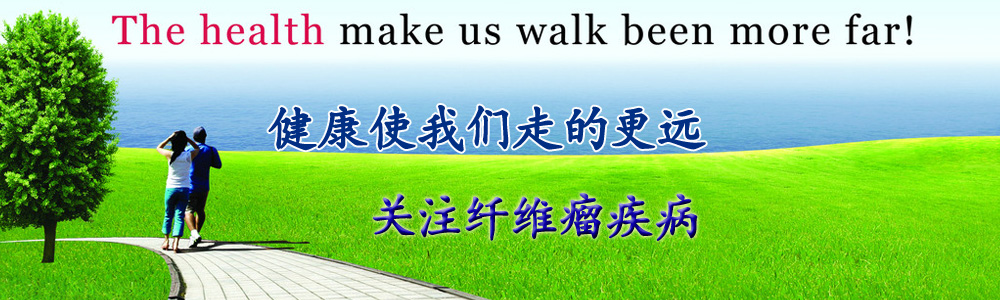知青岁月知青战友眯眯用三只眼看
#知青#
眯眯
薛建茹
眯眯,是我同连的战友。因其上眼睑过长,总像闭着眼睛,于是得了这么个外号。他也不恼,一叫准应。慢慢地他的大号就很少再用。称呼眯眯,很自然亲切;称呼大号秦凤云,反倒带着几分戏谑。他的个子矮小,加之上眼皮长,若要与人对视,必须仰起头。他稍稍有些驼背,走路不像小伙子,有点像个小老头。
一次,加工班连夜修理播种机,哥几个照顾他体弱,让他只管提着马灯照亮儿。机器修好了,大家往连里走,却不见照亮的眯眯跟上来,回头喊他,只见眯眯往下蹲,大家围上来,才知道他已冻得走不动了。播种时节的夜晚,气温还是很低的,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,早已僵了。最后,还是大伙把他架了回去。
还有一次,加工班的人,唯恐屋里不暖,把烟囱直直的从屋顶伸了出去。房子是原农场建造的,屋顶是用芦苇扎成的草捆铺成。那草捆扎得真地道,既瓷实又均匀,有两三拃粗细,一捆紧挨一捆,铺在檩条上,完全不用椽子。草捆之上再苫上厚厚的一层掺上麦秸和的黄土泥,很保温。这种方法解决了河套地区缺少建房木材的难题。就地取材,因地制宜,既经济又实用。加工班利用加工农具的方便条件,自己打制烟囱,再加上有供打铁用的煤炭,就没顾忌地烧了起来,直烧得挨着炉子的半截烟囱红透了。屋外天寒地冻,屋内温暖如春,哥儿几个舒舒服服地钻进了被窝。
全不知“曲突徙薪”的古训!半夜,草房顶烤着了,浓烟呛醒了暖暖深睡的几位。顾不上多穿衣服,拎上水桶,到井台取水。井台在加工班百米开外。眯眯力气小,负责摇辘轳,大家往回拎水。几个人在黑夜里穿梭似地跑着,不敢声张。一时间没有扁担,只能手提。磕磕碰碰,衣裳裤子都溅湿了。湿了的衣裳立刻结了冰,穿在身上如同铠甲。总算扑灭了火,大伙抽着烟,商量着如何在天亮之前收拾残局,别让领导发现。这时才发现跟前缺少眯眯!赶快到井台去找。只见眯眯坐在辘轳把上,井绳上还吊着一桶水。他为了供上水,不耽误时间,先摇上水来等着,为了省力,他用自身的重量压着。眯眯和大家一样,只穿了一条秋裤。别人是剧烈运动,他是基本不动等在那里。井台高出地面一米多,处在营房正中的大空场上,冬天的深夜,毫无遮拦。大家接眯眯的时候,他已经冻得说话都不利落了:“你……你们……把……把我……忘了吧?”
眯眯在加工班,好像什么都干,真好像阿Q的本事,舂米便舂米,撑船便撑船。木工?铁匠?好像都不是,反正交到他手里的农具或其他物件,都能修理好。他给车子补过车胎,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给大伙补鞋。他补鞋的工具箱里,家伙式儿挺齐全,手艺更是没得说。给大伙补鞋也收点工钱,左不过一毛俩毛。这点碎银子,大约添置过一些补鞋的针线,其余的就烟酒了吧。据会计说,从未交过柜上。
总仰头看人有点累,若不遇重要的人或事,一般他不抬头。久而久之,练就了特殊的本事,他曾经骄傲地说:“不用说话,只要看脚,我就知道是谁。”要知道,那时大家穿的鞋基本一样,各色的并不多。
返城时,大家都是光棍一条。谁也没想到,眯眯在老家早已结婚,并已有了两个孩子。儿子都快上学了。他竟然瞒得这样严实,跟媳妇愣是几年不通一封信!这在整个兵团恐怕也是独一份!原来,第一次探亲时,他父亲就让他在老家成了亲。论说做父亲的为儿子考虑的不可谓不周到、不深远,使儿子将来不必老死在边疆,所以早早给他安个家。
他父亲还把很多生活的高招传授给了儿子。例如,教给回城后的眯眯如何使用出差补助费。当时的补助,全国有统一标准。记得眯眯说一天的补助可以买十几个油饼,出差天津的话,当天打来回,早上吃几个,中午吃几个,晚上吃几个。这样既吃得饱又吃得好。完全不用往里搭钱。
眯眯得了一种病,皮下长了许多纤维瘤,越来越严重。不知他的早逝是不是与此有关。
作者:薛建茹,年生于北京。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三连。年至年北京街道纸盒厂。年至年师范大学读书。年至年在学校教书。年退休。
来源:兵团战友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hmwyc.com/qwlbzz/1354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百病从寒起,袪病先除寒艾灸穴位,改善寒
- 下一篇文章: 高能慎入孟加拉男子得怪病全身长满神经纤